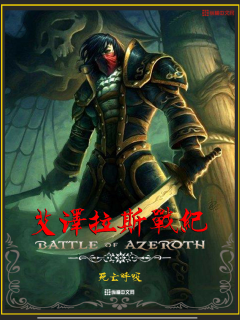讲到这里,你是不是有点失望?如果你觉得很无聊很无趣,那就对了。
如果因为你以前没上过学不了解这段历史而觉得无趣更正常。
呃……刚才是谁说要我从头讲的来着?
这段经历对我个人而言不美好,没有多么惊心动魄的值得纪念的地方。你们里面有达拉然的魔法师,有已经能呼唤圣光的骑士,也有一些多少会些小魔法小把戏的家伙。
如果你期待漫天的火球术炎爆术,时空扭曲,圣光拯救,暗影魔法的话,那你得失望了。
实话告诉你这段时期的经历里这种情况的并不多,当然未来也没那么多。
你们这几个掌握魔法的家伙是人群中拥有特殊天赋的,你们应该能知道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剩下的你们这些只能拿刀剑跟人以命换命的也不用生气,这个世界上没这方面天赋的普通人占绝大多数。所以不会有那么多大魔法师,尤其是最高等的那一类。随随便便毁天灭地的那是传说,我这是故事。
你们达拉然从创建到现在能被人称道的叫得出名号的魔法师其实也就那十几位,一两百年出一个天才才是常态。当然,我也不是瞧不起你们几个,魔法这玩意太吃天赋。曾经的守护者艾格文,麦迪文和卡德加这种人都是奇葩中的奇葩。
想当年……在希尔斯布莱德,被兽人进攻压得几乎绝望的时候,白银之手才建立,当时也算是名将如云了,现在暴风城英雄谷的雕像上好几个也都在,但是真正掌握圣光魔法的有几个呢?
那个谁……加文拉德,暴风王国圣骑士团曾经的领袖,以及死在诺森德的……伯瓦尔大公,还有这次远征的元帅之一的格雷森公爵,这些家伙你们都知道的,他们算是人中翘楚了,可魔法这玩意……太挑人。有天赋就是有天赋,没有天赋掐死你也憋不出半个火星子来。
这让我忽然想起……曾经真正的我。
呵呵!这个答案我寻找了几十年,现在当然记起我是谁了。
在曾经的未来我其实是一名神职人员。
怎么?很吃惊么?
得了得了,一会我会讲到怎么想起自己是谁的,不用着急。
你着急我也不会快进给你讲。
来到这个世界这段最初的经历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不爽。哼,或许也是冥冥中注定的事情吧。
在我的世界里,我经常接触死亡,以及和死亡相关的事情。
那些苦难的,卑微的,可怜的,等待救赎的人……普通人们,他们跟死亡的距离太近。真的太近。
当然你们这群家伙也是。你们中有些年轻的生命很快就会消失,仿佛从未出现过,没人记得你,甚至你的尸骨都不会回到故乡。
我没有危言耸听。
你们几乎没有可以抵御死亡的本领。
当然,你身上的铠甲可以让你多活一会,前提是在你运气别太差的情况下。
我经常见一些穷困的底层人,那些一脸苦相眼神中却偶尔闪着一丝狡黠的穷人,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苦难,悲哀,以及罪恶,我才知道这个世界的人竟然会如此的不同。
我不认为你们天生有罪,你们也不必为了什么去恕罪,说你天生有罪的人都是骗子。但是人真的有善良和不善良,聪明和不聪明,智慧和不智慧。
呵!有人对我说的这些是不是有点不耐烦了?没关系,你就是这六类人中的一种。
不!不不不!你说错了!没有勤劳不勤劳之分。勤劳不是美德,只源于生存环境。
为什么我突然有这么多感慨呢?
哈!人啊,只有感受过磨难才会……呃不,应该是极致的磨难甚至死过一回才能明白这些废话是什么意思。
你问我那晚死没死?
哈!你这个小机灵鬼。
你猜呢。
再次感觉有了意识的时候是被冷风吹醒。
前面说过我原本是在战场上,在诺森德的冰天雪地之上展开了一场极其惨烈的厮杀。所以冰冷的感觉很熟悉。
当冰冷的感觉唤醒我的时候内心是比较喜悦的。毕竟是活下来了,输赢未知也无所谓了,活着才最重要。
叮叮铛铛的铃铛声传进耳朵,我明白此时大概是在一辆马车或者牛车上,负了伤正被转运。
尝试睁开眼睛,只觉光越来越亮,甚至还有点刺眼。干涩的眼皮刮蹭着同样干涩的眼球,缓缓睁开从眼缝里看到了一抹湛蓝。那是独属于天空的颜色。
那是一种无比纯净的蓝!
风拂过脸,是冰冷的感觉。车子摇摇晃晃,天空也摇摇晃晃。冷飕飕的风钻进了我的身体里后化成一缕白雾又从嘴巴缝隙里冒了出来。
刚才那段记忆,这些天的经历仿佛是一场戏剧画片,断断续续地让我感觉是一个梦。
你不用嫌弃我总是脑子不清醒,你个傻哔。
过几天你在战斗中有幸被兽人用锤子砸了脑袋但是没死的话,你会理解刚讲的这种感受是怎样的。
我扭脸转了转眼珠子。一边是干草,毛皮,车上也只我一人。
就在想翻身看看周围什么情况的时候后腰和肚子上传来的剧痛叫我立马老实。
哈!有意思的是这时我竟没反应过来。
你懂我说的意思吧!
我没有丝毫怀疑此刻躺在牛车上的我有什么不对。
又躺了好一会,我想喊驾车的人一声,但嗓子好渴发出的声音低沉且嘶哑。强忍疼痛尝试着抬头看看是谁在驾车,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佝偻的背影。
“醒了也别乱动。”他扭过头瞟了我一眼。
没能看到这人的脸,听声音很苍老。
“我在哪?”实在不敢用力说话,胸膛里一点劲都使不上,一使劲后腰就好疼。
“一个安全的地方。”
“战斗赢了么?”
他没接茬。
“我竟然没死啊……”这不算感慨。
“你现在依然是个准死人。”那老头语气并不比这天气温暖多少。
“我们在撤退么?”
“你最好别说话。”他说:“留点力气多喘几口气吧。”
“我们……”忍痛撑起身子,我目光翻越车挡板眼前景象映入眼帘的时候感觉思维又陷入了错乱。
在这冰天雪地里就这一辆车,俩人!我跟赶车的老头。而且周围不是一望无际的冰原而是林海雪原。
“这是哪?”我扭头看向那家伙。
随着马车摇摇晃晃的背影根本无动于衷,过了好几秒才缓缓说道:“你不必知道。”
“那你是谁。”我努力提高声音。
“你不需要知道。”声音毫无感情。
这话叫我疑惑,但更叫我愤怒,“你要带我去哪!”
“奥加兹。”他终于回答了一个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那是哪?”当时对这个名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啊……那个矮人,我看到你了!你的表情说明你知道这个地方!
“到了你就知道了。”那老头又说半截话。
“我们是在诺森德么?”
听到这话那老头扭过脸来,苍老的脸上被岁月凿刻的痕迹非常明显。“你说什么?”
“这是哪?我们要去哪?”
“丹莫罗。”他说:“去哪我不是告诉你了。”
说实在的,当听到“丹莫罗”这个地名的时候我依然没反应过来。
“为什么带我去那里?”
他没立即回答我而是顿了顿说道:“我只负责把你送过去。”
“这里不是……诺森德么?”看着他那双没有任何感情的眼睛我满肚子疑惑。
“你最好躺下休息,睡觉晕厥都可以,总之不要说话,我可不会因为你脑子错乱胡言乱语而对你客气。”他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分明是威胁。
我当然没有听他的乖乖躺下,而是往周围张望妄图得到一些信息,老头也扭过头去不再理我。
这里森林茂盛,周围一片冰天雪地,诺森德也是一片冰天雪地,可我驻扎的地方不长这种冷杉也没有这种铁皮白桦。我不记得诺森德有个叫丹莫罗的地方,而至于那个什么奥加兹……脑海里更是完全没印象。
冷风又从领口灌进去,我只好重新躺了下去。“你要送我到那个奥加兹去是为了什么?我是被俘虏了么?”
“我不知道。”
“那是谁让你送的?”
“我不认识。”
这话叫我心里窝火,这不是放屁么?我在心里暗骂。“不认识就敢送我?”
“我为什么要认识?”
哈!“我又不是货物。”
“没区别。”他说得随意。
“我们走了多久了?”
他没吱声。
“这需要保密么?”
“我没有回答你的义务。”他的话跟空气一样冰冷。
“战争怎么样了?”
“你最好闭嘴。”他不耐烦了。
“你想怎么样啊?”我也生气了,“你告诉我还怎么了?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只负责把你送到地方。”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但不保证死活!”
老头眼神忽然变得犀利,尤其是那眼皮薄的像纸还没有眼睫毛的三角眼,眼白多瞳仁少,那种冷漠但凡不是个傻哔都看得出这绝对不是个善茬。只有杀过人而且是经常杀人的人才有这种眼神。
我果断闭嘴并老实躺了回去。
如果是安静地躺着应该会好些,可现在颠簸摇晃的马车上是不可能舒服的了。感受着肚子和后腰传来的不适,我还想着回忆起关于那场战斗以战争以外的一些事情,但脑子只有一片空白。而对于身上的伤更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完全不记得是被谁捅了刀子。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脑子里一下浮现出那夜的情节时,脑袋嗡的一下,一股转瞬即逝的剧烈疼痛感叫我叫出了声。
“我们离暴风王国……呃,东谷伐木场远么?”疼痛消失后我歪头使劲喊道。
过了好久,他才吐出了这个词。“远。”
“我们不在暴风王国的地盘上了对么?”
他似乎嗯了一声,我不确定。“对么?”我又问了一嘴。
“对!”他轻轻侧了下脸完全不耐烦。
这句话叫我如坠深渊!
“我是谁?”这句话脱口而出。
老头没吱声。
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心也跳得越来越快,一种压抑的郁闷的担忧的情绪立即占据我的内心,这也让我的情绪开始变得愈加烦躁。
冲天的大火,痛苦的哀嚎,凄厉的嘶吼,无助的呐喊,轰然的倒塌,恍惚间看到了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
黑影,有个黑影!
腰上突然抽搐了一下。
我尽量强迫自己打消这个念头,但越不想回忆就仿佛有人在我耳边不停提醒我一样。
努力翻了个身,麻木的双腿和腹部传来的剧痛扫除了一切杂念,随即使劲往肚子里吸了口气,强忍着腰腹部的疼痛,把一腔的气给压了出来。
老头赶紧勒住了缰绳并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你怎么了?”他盯着我。
我也盯着他干枯脸上那双犀利的眼睛,“是不是艾德温叫你把我送到这里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是谁。”
这回答叫我更加恼火,“你知道什么?他想干什么?”
“我只负责把你送到目的地,小子。”他面无表情。“颠簸会让你疼痛但你死不了,前提是你不找死的话。”
我看到了他胸前的匕首。
“你能不能活着到那里委托人可没另提要求。”
“你他妈放屁!”我咬牙切齿。“如果不保证我的死活我他妈早就死了。”
“我可以保证你不被熊吃掉,但你病死在路上我没有任何责任。”说着他伸出马鞭朝我肚子上戳了戳。
夜色清冷,篝火旁的老头似乎没有要把我扶起来的打算。
还没到黄昏老头就开始找地方准备过夜,这我没意见,可他完全拿我当空气,他不会问我要不要喝水,也不会问我要不要拉屎拉尿。现在夜幕降临,他只是自顾自地烤肉吃东西,我则在车里被晾到现在。
最后我咬牙爬了起来。
“你最好躺着别动。”他知道我过来却眼皮都不抬一下。
“躺着不动时间长了会死。”
“如果再出血了,你一会就得死。”他说话特别噎人。
尝试坐下这个动作就费了老大劲,可这老头依然自顾自地摆弄着手里的碗。
使劲咬了咬牙后我尽量温和地说道:“很抱歉白天对你说的话……脑子就是有点乱。”
老头没搭茬。
“到奥加兹还要几天?”
“取决于你。”他说,“伤口如果愈合得好,可以走快点。”说着他举了举手里的碗:“站起来,换药。”
看着脏兮兮的带血的绷带和有点感染的伤口我心里一阵别扭,“我躺了多久?”
“很多天。”
“是几天?”
“记不清。”如果不是一边的篝火这老东西的语气冷到结冰。
“丹莫罗是哪?我不记得暴风王国周围有雪山。”
“这里是矮人的地盘。”他这才说。
我惊讶得睁大了眼睛。“都已经到矮人的地盘上了?”
“看来已经走到足够远的地方了,但……去奥加兹似乎不经过这条路吧。”我故意这样说。
他只冷哼一声。火焰映照着他直勾勾盯人的眼睛和弯曲的鹰钩鼻子。真不像个好人。
“你的伤口几天前感染了。”他说:“虽然到终点无所谓你是不是一具尸体,但如果拉的是一具尸体总是很晦气。不过你要是真死了……”他欲言又止却没有停下手里的活。
“怎样?”
他终于抬起眼皮看向我,“你不会希望那样的。”
“那会怎样呢?”
“砍下你的头和左手带回去。”他的语气跟呼吸一样理所当然。
“那真是要谢谢你了,可我的头值多少钱?”我撇了撇嘴。
“不值钱。”
“我是梅森……对么?”看着他的脸我问道,“梅森•范克里夫,你应该知道这个姓氏。”
“无所谓你叫什么,梅森,杰森,安德森,还是什么别的玩意,你的头到底值不值一个铜板到了奥加兹就知道了,当然,如果你还能活着的话。”这份轻蔑我无法反驳。
“艾德温付给你的钱就是我脑袋的价格。”我说。
“你说的艾德温并没有付给我一分钱,而且付给我的钱就是你脑袋的价值的话,那你该失望了。当然,如果真如你说的这么值钱的话,我很乐意把你的头带回去。”老头说。
“带回去给谁?”
“这是个好问题,给谁呢?通缉榜上不知道有没有你的名字,既然你想试试,我也完全可以满足你。”老头的眼神充满了挑衅。
“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我既不想知道你叫什么,更不在乎你是哪个。我只给你一条忠告,你最好把自己当成一个哑巴,特别是有旁人在的时候。”
我皱了皱眉头,但转念一想觉得还是得听这个老头的话。
“你是怎么把我带过来的?”
“你看不见么?”他没好气。
“我是说……你……是如何将我带到这里的?全靠马车?”
“不然呢?”
“在我印象里……暴风王国北边是无人区吧,而且那里可不怎么太平。”
老头没说话。
“能告诉我么?”
“第一次听货物问送货人是怎么送货的。”他哼了一声,“你好好活着不好么?”
“这些问题至少得弄明白不是么?”
“我警告你……”他盯着我的眼睛说道:“该让你知道的我会告诉你,不该让你知道的我大概也不会知道,而且……我已经说过一次了,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小子。”
“你没有必要对我隐瞒什么。”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呢?你现在这个样子大概也不是什么好玩意。我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虽然送了你一路,但也可以随时送你上路,只要你不烦我的话。”
“哈!你他妈的!从头到尾都遮遮掩掩!瞒着我有什么好处!去你的放哑屁!他妈的!你去死吧!”
大叫一声我抄起了地上的劈柴。